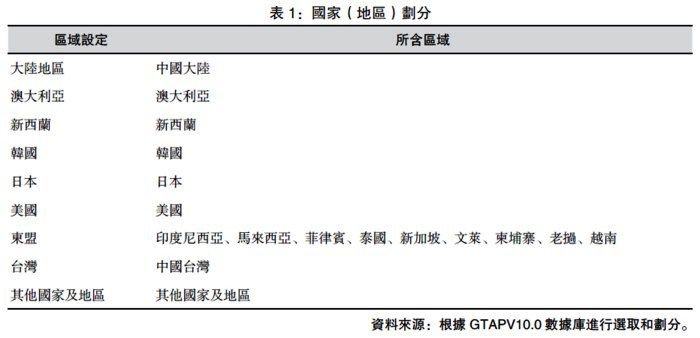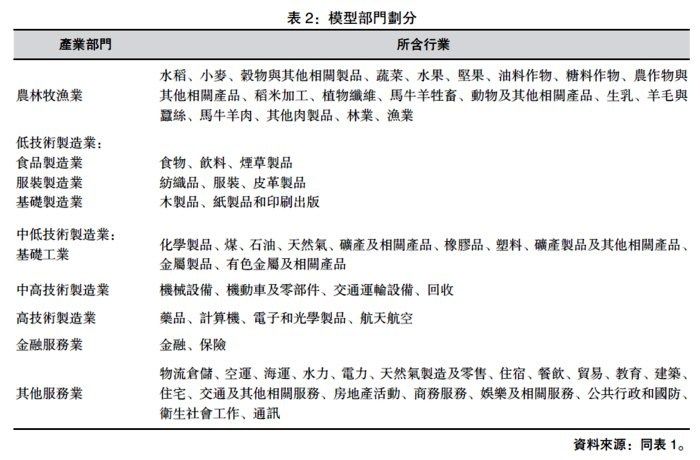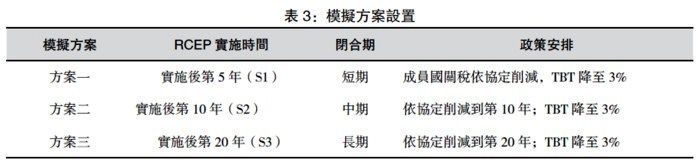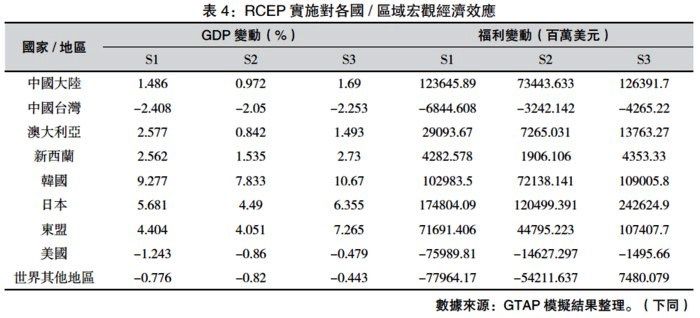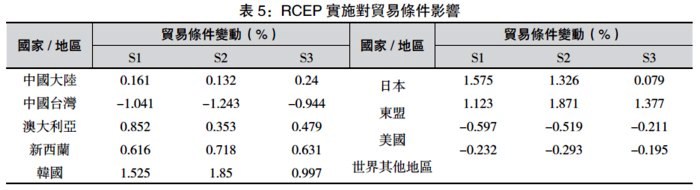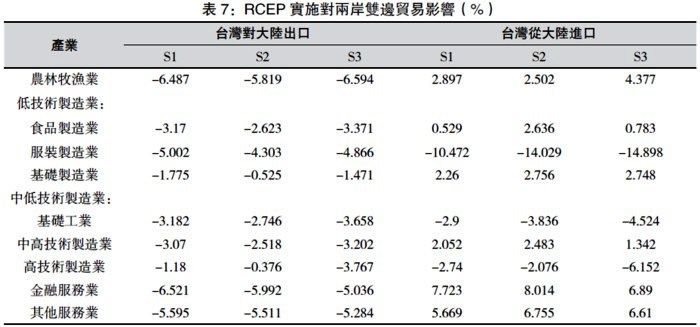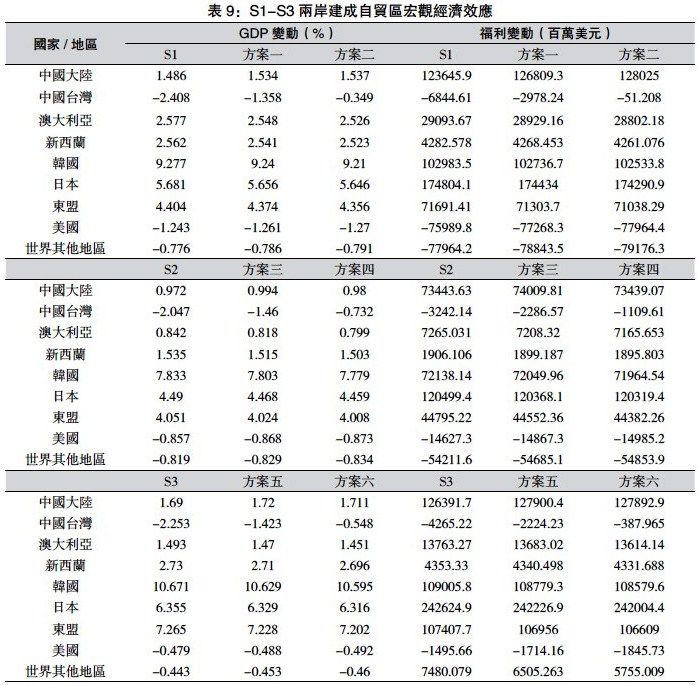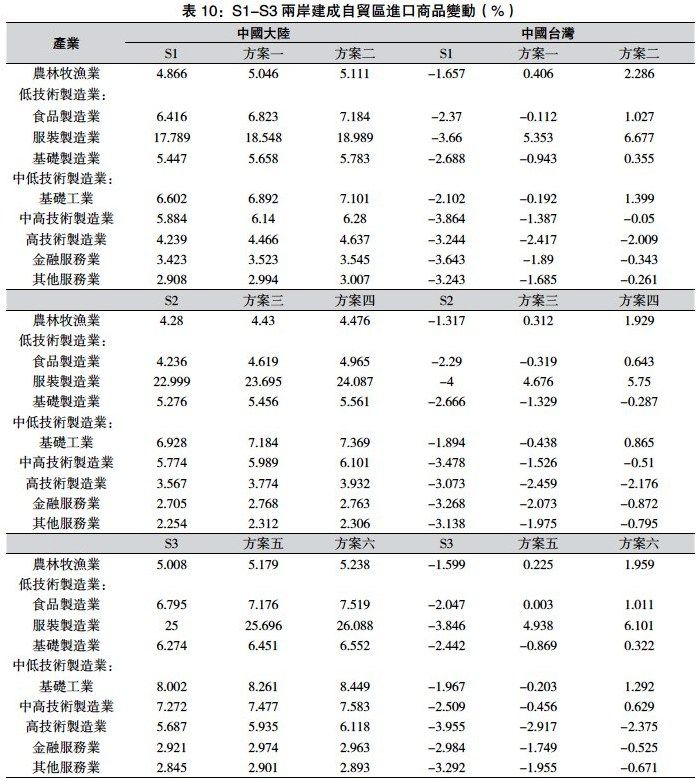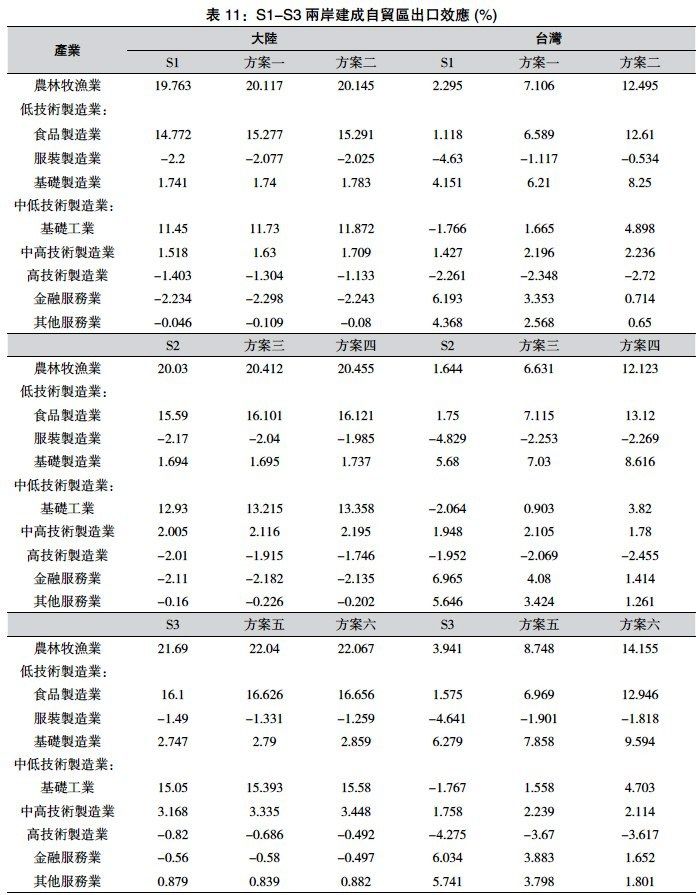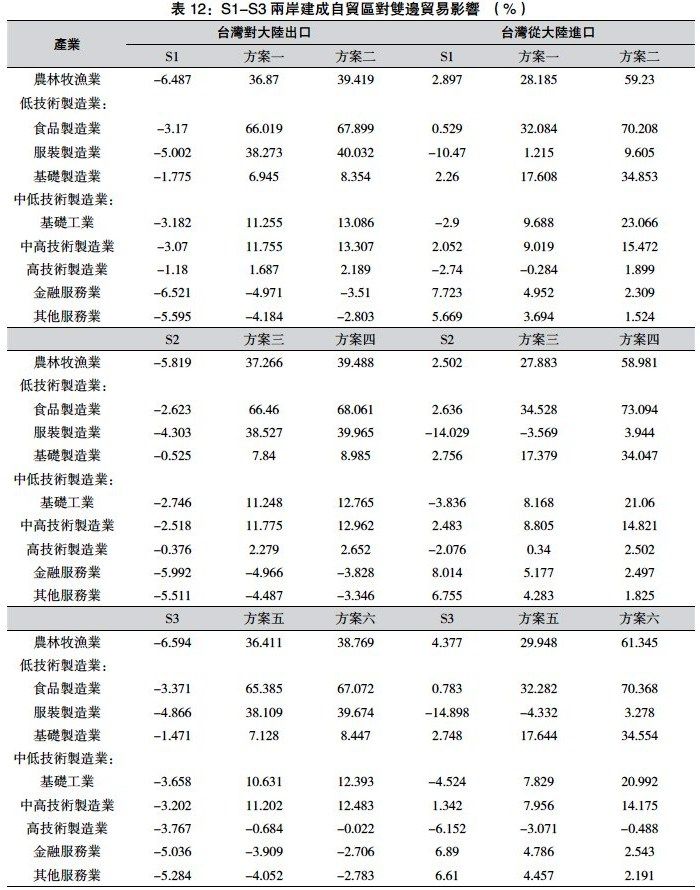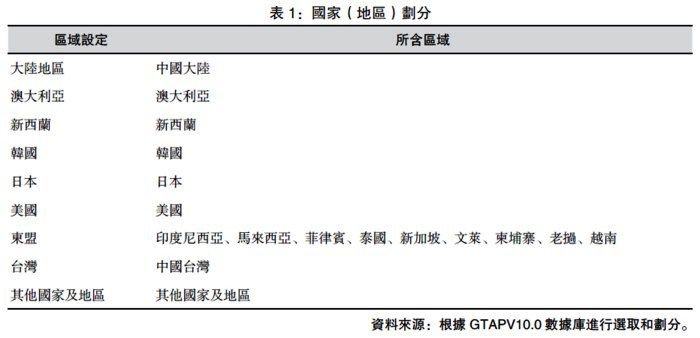
表1:國家(地區)劃分區域設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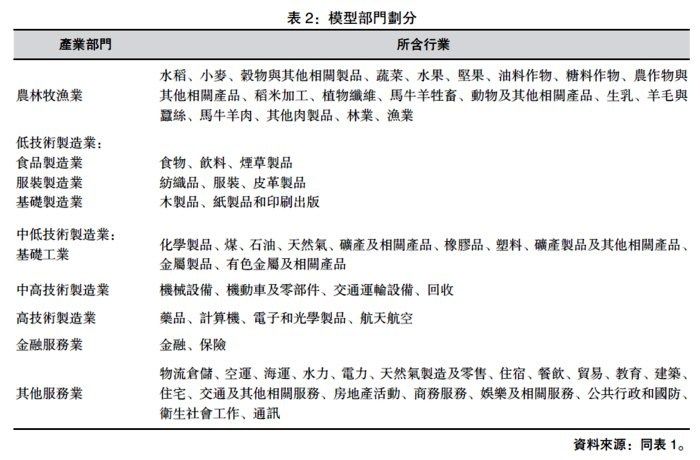
表2:模型部門劃分產業部門
中評社╱題:RCEP背景下兩岸參與區域一體化“輪軸”效應 作者:楊金發(福州),閩江學院海峽兩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院副教授;李文婷(武漢),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;林本喜(福州),福建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、海峽兩岸農業融合發展研究院院長、通訊作者
【摘要】RCEP作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里程碑,其實施將鞏固成員國的“輪軸”地位,卻可能使兩岸淪為“輻條”。本文通過一般均衡模型模擬分析發現,RCEP實施後作為“輻條”的台灣宏觀經濟、貿易及產業均面臨較大衝擊;而兩岸建立自貿區將助力大陸向“輪軸”國轉化,台灣能從與大陸的“輪輻”結構中獲益,且獲益幅度遠高於大陸。因此,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共建自貿區,促進兩岸產業“互補升級”,將是台灣脫離“邊緣化”的理性選擇。
一、引言
1979年《告台灣同胞書》首倡“三通”,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發表40周年之際強調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,夯實和平統一基礎;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,打造兩岸共同市場”。凸顯融合發展是大陸對台政策核心主軸。實踐中,大陸通過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(APEC)、與東盟簽合作框架協議、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(ECFA)、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(RCEP)簽訂等,構建起融入東亞一體化的制度網絡。反觀台灣因政治操弄,僅與新加坡簽自貿協定、與日本簽投資協議,ECFA到期未續簽且無緣RCEP,淪為“邊緣經濟體”。
東亞經濟一體化以中間產品貿易為主〔1〕,易形成“輪軸-輪輻”結構:“輪軸”國吸引要素集聚享受規模紅利〔2〕;而“輻條”地區受原產地規則限制面臨貿易轉移與產業空洞化〔3〕。RCEP生效將固化該結構,未加入該協定的台灣所受衝擊尤甚。
研究表明,“輻條”之間締約可對抗這種不利衝擊,降低“輪軸”國福利〔4〕,小型經濟體可通過與大型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(FTA)扭轉“輻條”困境〔5〕。當前兩岸同為“輻條”,RCEP對其經濟影響如何,兩岸應如何應對,亟待探究。本文采用全球貿易分析(GTAP)模型,根據RCEP關稅承諾表,研究其實施對兩岸“輪軸”效應的短、中、長期影響,及兩岸建立自貿區後的結構變化。首次量化評估RCEP對兩岸宏觀經濟與產業的異質衝擊,及兩岸FTA破解“輪輻”困境作用,為“九二共識”框架下重啓兩岸經貿談判提供依據。
二、文獻綜述
(一)FTA經濟效應的傳統框架
Viner(1950)提出“貿易創造效應”和“貿易轉移效應”,為自貿區福利分析奠定基礎。多哈回合受阻後,區域貿易協定(FTAs/RTAs)成了更現實選擇〔6〕。Bhagwati(1995)以“意大利面碗”形容FTA規則碎片化可能抵消多邊自由化收益〔7〕。Wonnacott等(1995)系統闡釋“輪軸-輪輻”結構:輪軸國與多條輻條分別締結FTA,輻條間無協定,使得輪軸國在貿易、投資及規則制定上享有不對稱優勢〔8〕。Puga等(1997)以D-S框架證明輪軸國因市場准入優勢引發企業集聚,放大收益〔9〕;而輻條國則面臨產業分散與福利損失〔10〕。
(二)“輪軸-輻條”理論的動態擴展
基於要素禀賦差異擴展體系,Deltas等(2006)指出輻條國間締約會降低輪軸國福利〔11〕;單純的輻條國數量增加會提升輪軸國福利,降低輻條國福利〔12〕。De Benedictis等(2006)以歐盟東擴為例指出輻條國互建自貿區動機強,輪軸國為避免淪為“輻條”也會構建自貿區以打破原有結構,為應對“輪軸”效應提供依據〔13〕。Lake等(2016)指出,晚加入的輻條國受原產地規則等限制發展受限,應積極開展貿易往來〔14〕。
東亞區域一體化推進中,學者聚焦該區域“輪軸”效應。李向陽(2008)據簽訂自貿區數量將新加坡視為“小型輪軸”國,提出小型經濟體需善用“輪軸-輪輻”效應,與大型經濟體締約爭“輪軸”地位〔15〕。Baldwin(2008)認為東亞可能出現中、日“雙輪軸”,形成類似“自行車”輪軸結構〔16〕。鄧慧慧和桑百川(2012)指出新加坡和東盟“輪軸”地位顯現,中國仍處於“輻條”地位〔17〕。盛斌(2014)則認為RCEP確立了東盟功能性中心地位〔18〕。
(三)兩岸視角的研究進展
學者關注到兩岸在東亞軸輻體系中的角色及布局。孫玉紅(2008)指出在東盟和新加坡為核心的“輪軸”系統中,中國面臨真實收入異化不利局面,應儘早與其他“輻條”締約〔19〕。彭支偉、張伯偉(2013)認為中國需深化亞太合作,構建以自身為輪軸自貿區網絡〔20〕。鑒於台灣仍游離於“輪軸”系統之外,季燁和彭莉(2013)認為台灣應構建以大陸為起點的自由貿易協定路徑〔21〕。
已有研究多為宏觀定性判斷,缺乏基於RCEP具體規則的動態模擬,更忽視對兩岸“輻條化”衝擊及“兩岸互連”對衝效應的量化評估。本文以GTAP10.0動態CGE模型填補此空白,首次將兩岸FTA關稅削減深度與階段路徑納入比較分析,為政策設計提供參考。
三、研究方法與模擬方案
學界常用GTAP模型研究“輪輻”效應〔22〕。該模型由美國普渡大學Thomas W.Hertel團隊開發,為多國多部門一般均衡模型,基於新古典經濟理論,假設市場完全競爭、生產規模報酬不變、生產者生產成本最小化、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及產品和要素市場出清。其生產函數為常係數替代彈性方程(CES),消費函數為彈性常數差(CDE)支出函數,國內外產品差異由阿明頓彈性方程體現。
本文采用最新GTAP10.0數據庫(2014年基準年),涵蓋141國(地區)和65行業。因RCEP於2022年生效,為更貼合現實情況,采用沃姆斯利動態遞推〔23〕將數據庫中的人口、熟練勞動力、非熟練勞動力、資本存量和GDP外推至2022年。GDP、人口數據源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,勞動力、資本數據源自法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,外推時GDP設為外生變量,技術進步為內生變量以實現模型閉合。
(一)區域和部門劃分
本文將全球141個國家(地區)劃分為9個區域:中國大陸、澳大利亞、日本、韓國、新西蘭、美國、台灣、東盟(不含貿易額極小的緬甸)和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(表1)。
[表1:國家(地區)劃分區域設定]
行業部門整合為9類:先按ISIC歸并為農林牧漁業、製造業、服務業;再依OECD研發密集度將製造業細分為4類,最終形成9大產業(表2)。
[表2:模型部門劃分產業部門]
(二)模擬方案設定
RCEP實施後,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超90%,將大幅降低區域貿易成本與商品價格;同時通過簡化通關、減少貿易壁壘等顯著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。參考劉冰(2014)的研究,模擬時將RCEP成員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(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,TBT)降至3%〔24〕。
RCEP涵蓋15個成員國因國情不同降稅周期各異,如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為20年,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為23年,韓國則承諾35年,實現幾乎全部產品零關稅。為全面體現協議影響,本文設短期(第5年,S1)、中期(第10年,S2)、長期(第20年,S3)三期模擬,具體方案見表3。
[表3:模擬方案設置模擬方案]
關稅減讓分“統一減讓”和“國別減讓”,降稅模式包括協定生效立即為零、過渡期降為零、部分降稅及例外產品。最終中國將對86%的日、韓國產品,對分別90.5%、90%、90%的東盟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產品實行零關稅。其他締約方對中國產品最終零關稅的比例均超85%,其中澳大利亞高達98.2%。關稅衝擊計算中,先將各國HS8位關稅平均為HS6位,再以進口額加權為GTAP57部門關稅,最終按產業貿易額權重整合為9類產業關稅。東盟合并時,先依各國與貿易夥伴的貿易額權重計算產業衝擊,再按其在東盟貿易額占比整合。
四、模擬結果分析
本文利用RunGTAP軟件按3種方案進行政策模擬,考察RCEP實施對兩岸宏觀變量及各類產業的進出口的變動,探究其“輪輻”效應。
[表4:RCEP實施對各國/區域宏觀經濟效應國家/地區]
(一) 對宏觀經濟的影響
RCEP實施後成員國GDP因貿易創造效應提升,以韓國、日本和東盟增幅最高;非成員國則下降。台灣GDP在S1、S2、S3分別下降2.408%、2.05%、2.253%,總體呈負面影響,且短期衝擊大於中長期;大陸GDP分別上升1.486%、0.972%、1.69%,長期影響最顯著。
福利變動方面,日本、中國大陸、韓國均大幅提升,台灣和美國福利水平損失較大。台灣在短、中、長期福利損失分別為6844.608百萬美元、3242.142百萬美元和4265.22百萬美元,短期衝擊最大。
表5顯示,RCEP成員國貿易條件均有改善。韓國、日本、東盟在S1改善最顯著,分別達1.525%、1.575%、1.123%。這與韓、日長期高關稅保護及農產品等敏感品例外不降稅有關。而台灣和美國貿易條件則惡化,台灣S1至S3貿易條件分別變動-1.041%、-1.243%、-0.944%。中國大陸貿易條件則小幅改善,同期分別上升0.161%、0.132%、0.24%。
[表5:RCEP實施對貿易條件影響國家/地區]
可見,RCEP強化了新加坡、日本等“輪軸”國地位,台灣作為“輻條”受衝擊顯著;中日經貿得到促進,但日本作為“輪軸”受益更多,中國大陸受益有限。
(二)對兩岸產業進出口及產出的影響
出口方面,RCEP對兩岸影響顯著。大陸服裝製造業S1至S3分別下降2.2%、2.17%、1.488%,顯示東南亞逐步承接中國大陸相關產業;高技術製造業分別下降1.403%,2.01%,0.823%,短期受韓、澳、日等國商品擠壓,長期則因產業升級而緩解。台灣的農林牧漁、食品製造等行業受影響較小,但服裝製造、高技術製造和基礎工業衝擊顯著。其出口主力機電產品(高技術產業代表)S1至S3分別下降2.261%、1.952%、4.275%,隨關稅削減衝擊加劇;塑料橡膠製品(基礎工業)亦受影響(表6)。
[表6:RCEP實施對兩岸主要產業部門進出口及產出影響(%)產業]
進口方面,大陸各產業進口均有提升,S1至S3服裝製造業分別增長17.789%、22.999%、25%,中低技術製造業分別增長6.602%、6.928%、8.002%,助力經濟結構轉型。台灣各產業進口均受負面影響,高技術產業受衝擊最大,同期分別下降3.244%、3.073%、3.955%。占總進口額42.7%的機電產品關鍵零部件進口長期衝擊更大,顯示其產業鏈地位受挑戰,呈“邊緣化”趨勢。
總產出上,RCEP助力成員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。大陸除服裝製造和高技術製造業外均增長;台灣受到“輪軸”效應影響,產業向自貿區內轉移,服裝製造、基礎工業等均受波及,尤其是服裝製造業S1至S3分別下降3.247%、3.047%、3.115%(表6)。
(三)對兩岸經貿影響
表7顯示,RCEP實施對兩岸經貿產生負面影響,且隨時間推移雙邊貿易呈惡化趨勢。台灣對大陸出口所有產業及自大陸進口商品均遭波及,體現出兩岸經貿在各產業層面聯繫的緊密性。
[表7:RCEP實施對兩岸雙邊貿易影響(%)產業]
五、兩岸一體化效果模擬
“輻條”間簽署FTA可拓補“輪軸-輪輻”結構,提升自身福利、降低輪軸國福利,且“輻條”間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“輪軸”效應越弱〔25〕(鄧慧慧,桑百川,2012)。兩岸同為東亞“輻條”,建立新FTA可打破原有結構弱化“輪輻”效應;尤其在RCEP生效後,台灣融入區域一體化更需大陸支持。為此,本文模擬RCEP實施下兩岸建立FTA對雙方“輪軸”效應的影響。
參照兩岸ECFA早收清單(大陸對台539項、台灣對大陸267項產品分三階段降至零關稅),結合大陸降稅力度更大特點,分兩種情況模擬(暫不考慮貿易便利化影響):S1至S3分別設方案一(大陸對台零關稅+台灣對大陸關稅減50%)和方案二(兩岸互相零關稅),共計6個方案,具體如表8。
[表8:兩岸達成自貿區政策模擬方案模擬方案]
表9顯示,兩岸達成新FTA對其他經濟體影響有限,但對兩岸均有顯著積極作用。大陸GDP在方案一、二下分別增長1.534%、1.537%,高於S1情景的1.486%;福利水平也較S1提升。但台灣進一步削減對大陸進口關稅,對大陸GDP和福利提升作用不明顯。
[表9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宏觀經濟效應國家/地區]
對台灣而言,與大陸達成新FTA將顯著改善其宏觀經濟。對比S1情景,方案一、二下GDP降幅從2.408%收窄至1.358%和0.349%;福利損失也從6844.61百萬美元降至2978.24百萬美元及51.208百萬美元。其改善幅度遠超大陸,表明台灣對兩岸經貿依賴度更高。且對大陸商品降稅力度越大,其自身GDP和福利改善越顯著,凸顯其主動開放至關重要。
結合S2、S3階段,兩岸一體化在各期對雙方均有積極影響,且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。各階段台灣受益都遠高於大陸,對大陸降稅力度越大改善越明顯。表明加強兩岸經貿合作可減少台灣作為“輻條”受損程度,貿易自由化程度越深改善幅度越大。
表10顯示,兩岸達成FTA後,雙方進口規模均上升。相較S1情景,方案一、二下大陸所有產業進口均增長,尤以服裝製造業為最。表明這將進一步推動大陸經濟結構轉型,縮小低技術製造業貿易順差。對台灣而言,因RCEP導致進口規模下降得到顯著緩解,尤以服裝製造業為甚——從S1的下降3.66%轉為增長5.353%和6.677%。結合S2、S3情景,可見短期和長期對兩岸進口規模的影響更顯著。
[表10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進口商品變動(%)產業]
表11顯示,兩岸達成新自貿區協定對兩岸雙方出口均有積極影響。對大陸而言,受RCEP衝擊的服裝製造、高技術製造業均有所改善。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出口降幅從1.403%收窄至1.304%,台灣進一步降稅後更縮至1.133%,助力於大陸產業鏈向高端布局。其他行業也呈現增長,凸顯兩岸經貿合作的積極作用。
[表11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出口效應(%)]
對台灣而言,農林牧漁、食品製造業、基礎工業和服裝製造業出口顯著改善。如杜聲浩(2020)所述,RCEP將削弱台灣中低端製造業競爭力,而大陸廣闊市場有益於其相關產業出口、維持競爭力〔26〕。但高技術製造產業出口的小幅下降,表明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增強、兩岸產業差距縮小,過去產業互補格局正發生變化。
結合S2、S3情景,兩岸貿易自由化在短、中、長期內對雙方出口規模均有積極影響,并且台灣的改善程度顯著高於大陸。
從兩岸建成自貿區後進出口變動看,無論哪個時期,大陸進出口規模均將擴大,助力其向“輪軸”轉型;台灣作為小型經濟體,打破原有“輪軸”結構後其改善幅度明顯優於大陸。從時間來看,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,故中期階段兩岸需積極拓展經貿往來、深化合作,充分釋放兩岸一體化潛力。
表12顯示,兩岸自貿區建立對雙方經貿均有顯著積極影響。出口方面,各產業出口規模均有上升,以台灣食品製造業改善最突出——從下降3.17%轉為增長66.019%,台灣對大陸零關稅後更升至67.899%。進口方面,除了服務業以外,也均有較大增幅。結合S2、S3情景,隨自貿區建成時間推移,兩岸貿易規模將持續擴大,可見兩岸一體化在各時期對雙方貿易均有積極影響。
[表12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對雙邊貿易影響(%)產業]
六、結論及建議
本文通過GTAP模型研究發現,RCEP作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由“功能性”向“制度性”轉化的重要舉措,將強化區內成員國(地區)“輪軸”地位——東盟和日本在GDP和福利水平上顯著改善;中國大陸作為“輻條”宏觀經濟改善有限;而被RCEP排除在外的台灣則面臨較大衝擊,經濟增長、貿易條件下滑,高新技術和基礎工業受挫、產業外移,呈現被“邊緣化”趨勢。
兩岸同為“輻條”,貿易自由化是打破現有“輪輻”結構、提升雙方福利的重要途經。若兩岸建立自貿區,可顯著緩解“輪輻”效應負面影響:台灣受益遠高於大陸,且其對大陸越開放改善幅度越大。大陸亦可藉此擴大進出口規模,助力其向“輪軸”轉型。從時效來看,短、長期影響大於中期,故中期更需深化協商,推動更高水平合作以釋放一體化潛力。
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,實現兩岸融合發展,建議:台灣當局應在承認“九二共識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,主動與大陸共建自貿區,依托自身小型經濟體優勢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,藉助“輪軸”效應融入區域一體化。大陸需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,構建以自身為“輪軸”的自由貿易網絡,并且通過深化合作機制與信息共享,激發區域經濟活力和貿易潛力。
本文由福建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(編號:2023J011411)資助。
注釋
〔1〕張帆,《論 “後雁行模式” 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》,《國際貿易問題》,2003年第8期,第13-17頁。
〔2〕〔9〕Puga D, Venables A J,《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》,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》,1997年,第43卷第3-4期,第347-368頁。
〔3〕〔14〕Lake J, Yildiz H M,《On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Customs Unions》,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》,2016年,第103卷,第213-233頁。
〔4〕〔11〕Deltas G, Desmet K, Facchini G,《Hub-and-spoke free trade areas》,2006年。
〔5〕〔15〕李向陽,《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小國戰略》,《當代亞太》,2008年第3期,第36-49頁。
〔6〕Viner J,《The customs union issue》,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,2014年。
〔7〕Bhagwati J,《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: the wrong road》,《Law & Pol'y Int'l Bus.》,1995年,第27卷,第865頁。
〔8〕Wonnacott P, Wonnacott R J,《Liber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: New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》,《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》,1995年,第6卷第2期,第107-119頁。
〔10〕成新軒、張玉柯,《重叠式自由貿易區與多邊貿易協議的關係》,《南開學報》,2006年第5期,第118-124頁。
〔12〕東艶,《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模式——“輪軸—輻條”雙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分析》,《財經研究》,2006年第9期,第4-18頁。
〔13〕De Benedictis L, De Santis R, Vicarelli C,Hub-and-Spoke or else?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“enlarged” European Union》,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》,2005年,第2卷第2期,第245-260頁。
〔16〕Baldwin R E,《The Spoke Trap: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》,《China, Asia,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》,2008年,第51-85頁。
〔17〕〔25〕鄧慧慧、桑百川,《FTA網絡化發展中的“輪軸-輻條”模式:福利效應與中國的參與戰略》,《財貿經濟》,2012年第7期,第88-94頁。
〔18〕盛斌、果婷,《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》,《世界經濟與政治》,2014年第10期,第4-21頁。
〔19〕孫玉紅,《比較優勢與輪軸-輻條結構FTA成員的利益分配》,《世界經濟研究》,2008年第7期,第47-53頁。
〔20〕彭支偉、張伯偉,《TPP 和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及中國的對策》,《國際貿易問題》,2013年第4期,第83-95頁。
〔21〕季燁、彭莉,《台灣當局自由貿易協議實踐的亞太轉向及其前景》,《台灣研究集刊》,2013年第6期,第1-11頁。
〔22〕王庭東、錢進,《中日韓自貿區“輪輻”效應研究——基於要素集聚及產業視角的分析》,《東北亞論壇》,2017年,第26卷第4期,第28-41頁。
〔23〕Walmsley T L, Dimaranan B, McDougall R A,《A base case scenario for the dynamic GTAP model》,《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, Purdue University》,2000年。
〔24〕劉冰、陳淑梅,《RCEP框架下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經濟效應研究——基於GTAP模型的實證分析》,《國際貿易問題》,2014 年第6期,第91-98頁。
〔26〕杜聲浩、王勤,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對台灣的經濟影響 —— 基於價值鏈分析和GTAP政策模擬》,《台灣研究集刊》,2021年第1期(總第173期),第76-89頁。
(全文刊載於《中國評論》月刊2025年8月號,總第332期,P55-67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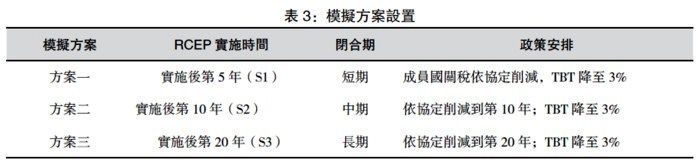
表3:模擬方案設置模擬方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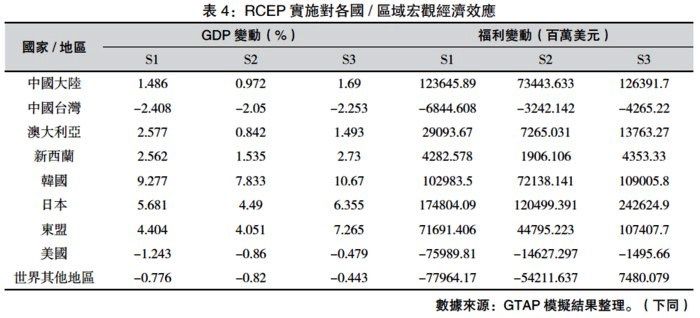
表4:RCEP實施對各國/區域宏觀經濟效應國家/地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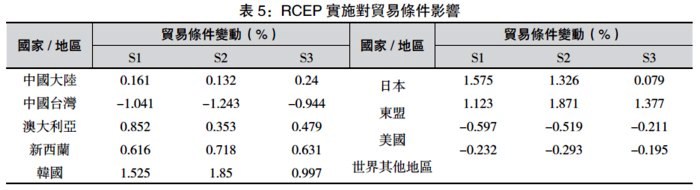
表5:RCEP實施對貿易條件影響國家/地區

表6:RCEP實施對兩岸主要產業部門進出口及產出影響(%)產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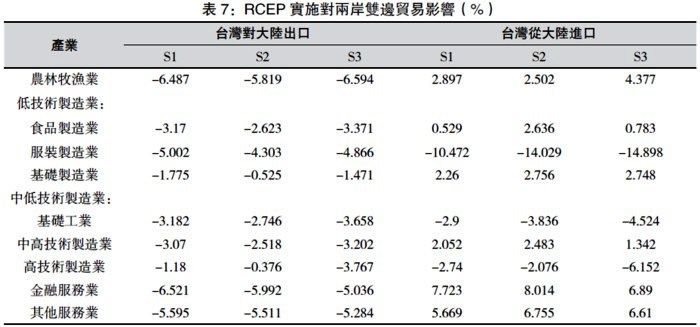
表7:RCEP實施對兩岸雙邊貿易影響(%)產業

表8:兩岸達成自貿區政策模擬方案模擬方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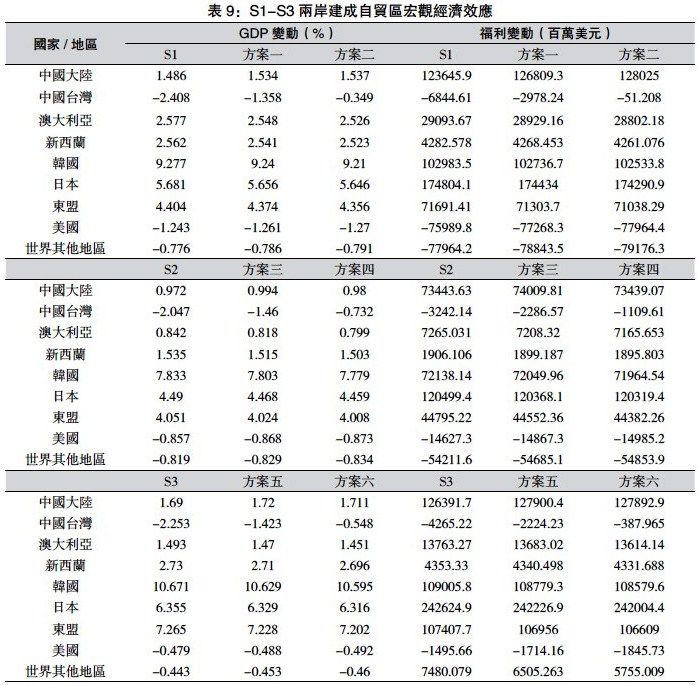
表9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宏觀經濟效應國家/地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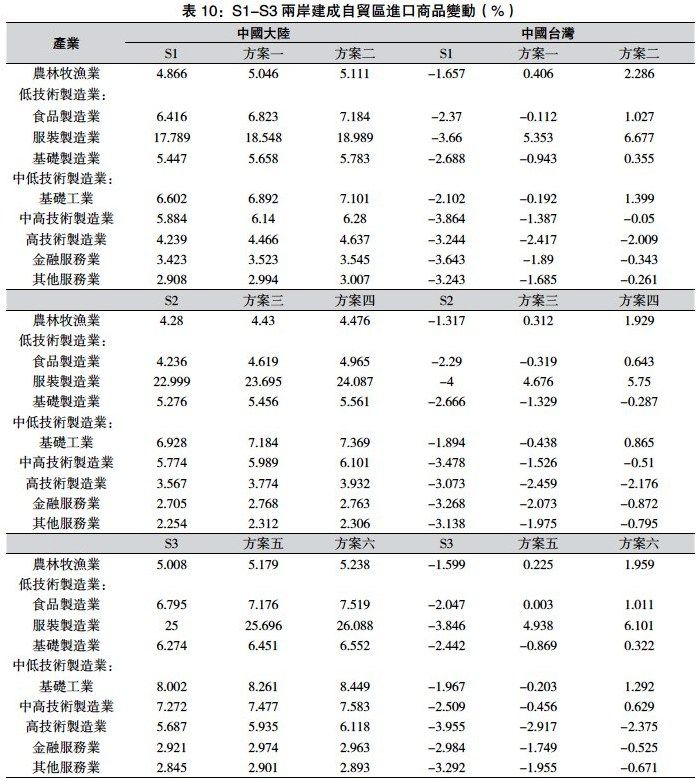
表10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進口商品變動(%)產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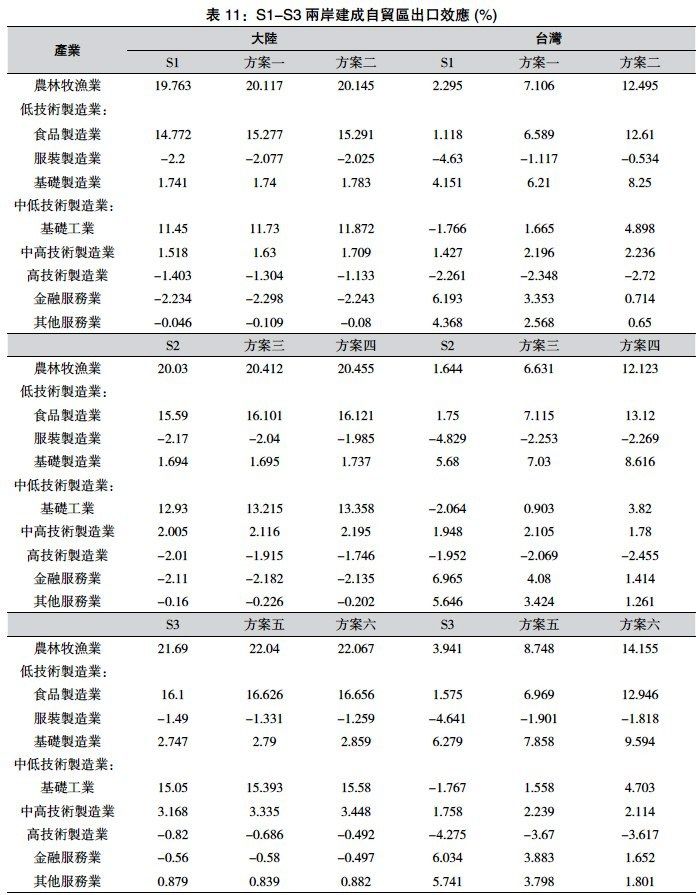
表11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出口效應(%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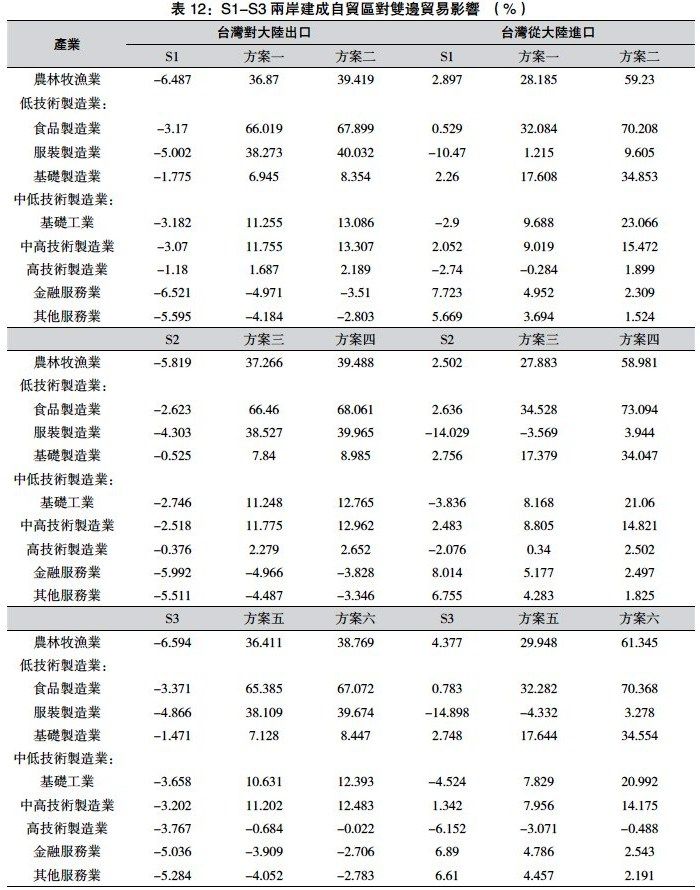
表12:S1-S3兩岸建成自貿區對雙邊貿易影響(%)產業